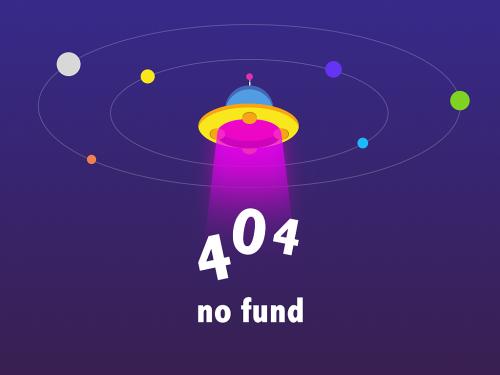满怀敬畏之心才能译出精品来
● 唐宝民
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始于中学时代。这些年来,一直没间断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也一直不间断地购买外国文学书籍,但我对外国文学书籍很挑剔,不是见到一本就匆忙买下,而是经过仔细翻看后才决定是否要买。我比较偏爱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外国文学译本,因为翻译水平比较高,那一代老翻译家,心态不浮躁,做事特别认真,经他们翻译出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上乘之作。翻译是一门艺术,只有怀着敬畏之心、抱着一丝不苟的态度的译者,才能为读者贡献出精品的译作来。
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一书的译者之一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卜立德,卜立德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翻译家,在翻译《寻找家园》过程中一丝不苟的态度,着实令人感动。高尔泰先生在新书《草色连云》中记述了其中令人感动的细节:“例如对《月色淡淡》中那位医生1958年在夹边沟农场说的话,同三十多年后我在美国读到的一位生物学家在书里说的话互相印证,他(指卜立德)要根据。有些专业术语,‘根瘤菌’、‘粒腺体’、‘原始细菌’等等,他要复核。直到我找出那位生物学家书中的相关文字,复印了寄去,他才满意。又如译《运煤记》,他问‘魏诗’是‘魏风’吗?我说是魏晋南北朝的魏,《采薇》是魏文帝作品。他问贵可称帝,怎么还‘薄暮苦饥’?……再如译《沙枣》,他问,十来个人的饭桶,‘比汽油桶矮些粗些’,有这么大么?一勺子半加仑糊糊,那就很多啦,怎么还吃不饱?这些量度,是我事后估计,未必准确。饭勺是铁皮的,半圆形的,近似半个篮球。桶是木桶,很厚,上大下小,有两块板子高出其余,左右对称,上有圆孔,可系绳以抬。一下子说不清,我画了个图,两人抬一桶,桶上挂着勺,给他寄去。他看了说,明白了。
”
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前辈,冯先生的译著之所以成为译坛经典,是和他在翻译过程中严谨的态度分不开的。有一回,冯先生去北戴河参加夏令营,他是带着工作去的,一边休假、一边继续翻译文学作品。那些天,他正在翻译美国作家海明威写的反映西班牙内战的短篇小说《在山冈下》,那里面有一段内容写到了西班牙政府军与佛朗哥法西斯部队的炮战,说“炮弹在政府军战壕上空飞来飞去”,这下冯亦代犯糊涂了,因为他搞不清这究竟是政府军的炮弹,还是佛朗哥一方的炮弹,他便苦苦思索,甚至还画了一幅地形图,但还是无法搞清究竟是哪一方的炮弹。就这样,那些炮弹在冯亦代的脑子里飞了一整天,他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晚上喝酒时,他又把这个问题向另外两个同行说了,三个人一起分析,可还是没有弄明白。冯亦代先生是个对读者高度负责任的翻译家,他不愿意让读者跟着一起糊涂,就终止了对这篇小说的翻译,把问题暂时存疑。回到北京后,他又查了很多资料,终于把事情搞明白了。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很久以后,那几枚炮弹,依然在冯亦代先生的脑子里飞过来、飞过去……
韩少功说:“翻译是一种精读。”能做好翻译工作的前提,就是对读者、对学术认真负责的态度。如今,常常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新闻:某个外语专业毕业的年轻人,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翻译出了一部上百万字的世界名著……对于这样的译本,我总是充满十二分的警惕:以如此速度完成的译本,其质量能保证吗?因为翻译不是油漆,不是你把白的刷成黑的、黄的刷成绿的就完事大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两个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相互之间的转换,复杂得很,表述清楚不是一件容易事,只有苦心孤诣、呕心沥血,才能达到“信、达、雅”的佳境,如此艰巨的工作,岂能一挥而就?用急功近利的心态加工出来的粗质滥造的所谓作品,能经得住考验吗?因此,我们要向以严谨治学态度从事翻译工作的翻译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严重鄙视那些心浮气躁、把名著糟蹋得不成样子的“翻译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