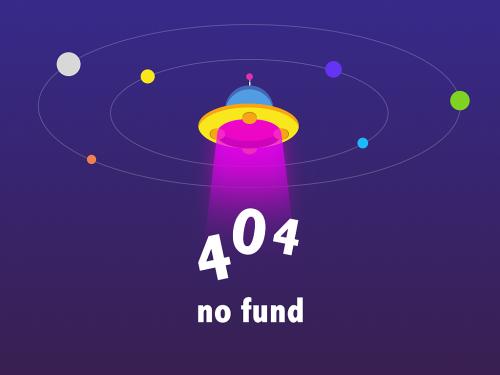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轻松掌握30种语言
柏林的天很是晴朗,阳台外面,tim keeley和daniel krasa两人正用言语「交战」着。先是德语,后是印地语、尼泊尔语、波兰语、克罗地亚语、(中国)普通话和泰语——对话中不同语言的衔接简直天衣无缝。总共他们涉及了大约20种不同的语言。
房间里,我发现一些小团体正玩着文字绕口令。其他的三人一群,准备一个「速射」游戏,内容就是同时口译出两种不同的语言。这简直不能让人更头痛了,但是对于他们而言,跟若无其事一样。「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常事」,有一个名叫alisa的人告诉我。
学习一门外语很难。但我现在在柏林一个通晓多语者的聚会上,会上大约有350人,他们都会说多门语言——语言范围很广,如有马恩岛语、克林贡语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驯鹿牧民说的萨米语。事实上,他们中有惊人的一部分还是「hyperglot」(会六门以上语言的人),如keeley和krasa, 他们至少会10门语言。
richard simcott是我在这里遇见的语言最熟练的语言学家之一,他在emoderation公司管理一个会多门语言者的团队,而他自己大概会30门语言。
较熟悉意大利语和会基本的丹麦语,让我在这群「hyperglots」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是他们对我说,我应该向最厉害的学习,因此,我在这里就试图去发现他们的秘密。
如果我们考虑关于大脑挑战的问题,也难怪大多数人会认为学习语言是多么苛刻。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记忆系统,掌握一门不同的语言需要所有的这些系统。
其中有一个程序记忆——肌肉的精致分布形成完美发音,还有一个陈述性记忆——记住事实的能力(如果想要达到母语者的流利度,需要至少1万的词汇,更别说它的语法知识)。除非你想听起来像一个结巴的机器人,这些词和结构必须在一瞬间从你的舌尖出来,这就意味着这些词和结构必须同时运用到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
多讲一门语言可以延缓痴呆五年
高强度的心智锻炼也是可以带来巨大回报的,它可能是你进行大脑训练最好的方法。众多研究表明会多门语言可以改善注意力和记忆,从而提供一个「认知储备」,这一「认知储备」可以延缓痴呆的发病。加拿大约克大学的ellen bialystock综观移民的经验,发现会两门语言可以延缓痴呆5年。会三门语言可以延缓痴呆6.4年,而那些会4门或者更多语言的人拥有比单语者多9年的健康认知。
这些持久的好处与绝大多数商业性质的「大脑训练」游戏的失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网络上下载的游戏通常不能长期改善记忆与注意力。
随着年龄的增大学习一门新语言比你想的要简单
然而,近年来有很多神经科学家指出我们大部分的人学习新语言的年龄太大,因而不能达到母语者的流利度。这根据的是一个「关键期假说」,这个假说假想在我们的儿提时代,有一个狭窄的窗口,只有通过这个窗口才能掌握一门新语言中细微的差别。但是bialystock的研究表明,这个假说被夸大了。她发现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学习语言的能力只有轻微的下降,而不是直线下降。
确实,我在柏林遇到的「hyperglots」都是在后来学会多门语言的。keeley在弗罗里达州长大,在学校他接触到的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常常收听一些外国电台——虽然他一个词也听不懂。「就像是音乐一样」,他说。成年之后他才开始环游世界——首先是哥伦比亚,在那里的大学,他学会了法语、德语和葡萄牙语。在去日本之前他到过瑞士和东欧。现在他可以流利地说至少20门语言,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是在他成年后学会的。所以他说:「关键期假说根本就是胡扯」。
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些「hyperglots」都是如何掌握如此多的语言,我们能够效仿他们吗?可以的,他们很可能仅仅只是比大多数人动力更足而已。像keeley一样,许多人都是环球旅行者,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边走边学语言,很多时候是关乎生存问题的。
但是,即使意图明确,我们中很多人在讲另外一门语言时,仍在令人满意的路上挣扎着。keeley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成为多语者的社会、心理和情感因素」的书。他怀疑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原智力的问题。他说:「我认为智力并不是主要原因,虽然它让我们更快地拥有分析能力。」
文化变色龙
相反的,他认为我们应该跨过智力因素,直达我们的性格。keeley认为学习一门新语言会让我们造出一个新的自我意识——最好的语言学家尤其擅长采用一个新的身份。他说:「你就成为了一个变色龙」。
心理学家早就知道我们说的话和我们的身份意识交织在一起。老生常谈的就是法语让人更加浪漫或意大利语让人更有热情。但是每一种语言和文化规范联系在一起,从而影响我们的行为——举个例子,就像你喜欢直言不讳还是喜欢安静思索一样简单。重要的是,众多研究发现多语者经常会根据他们所说的那门语言而采取不同的行为。
不同的语言也可能勾起你生活中不同的回忆——一个名叫vladimir nabokov的作家在写自传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现象。这个母语为俄语的作家非常艰难地用他的第二语言英语进行写作,期间,他发现「我的记忆都在一个基调上——俄语无声的音乐美,但是被硬生生扯到另一个基调上——英语」。作品出版后,他决定将这些回忆重新翻译成他孩提时代的语言。但是当俄语单词不断涌现,他发现他的记忆也跟着一些新的细节和视角不断展开。
「他的俄语版本如此不同以至于他觉得他应该重新将其翻译成英语」,费城坦普尔大学的aneta pavlenko在其《双语思维》一书中写道。该书探讨了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感觉作家的英语和俄语本身有着不同的过去。
反对再造过程可能会阻止我们学好另一门语言,keeley说,他现在是日本九州产业大学跨文化管理部的一名教授。最近,他在做一个关于中国人学日语的调查,来检测他们的「自我渗透性」——问题如「我觉得为他人着想,想象他们的感受很简单」或「我能给别人留下印象」和我们是否能够适应周边人而改变我们的观点。正如他所想的那样,那些在这些问题上得高分的人在讲一门新语言时流畅度更高。
这不仅仅只是关乎花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时间数量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众所周知,如果你认同某一个人,那么你更容易去模仿他——这个过程可以无不费力地改善语言学习。但是所采纳的新身份和相关的记忆可能会阻止你将母语和这门新语言弄混淆——通过在语言间设置神经障碍。「在我们的人脑中肯定有为每门语言和相关的文化与经历设置小隔间,以此来使各种语言保持活跃而不会相互混淆」,keeley说,「这不仅仅只是关乎学习和使用语言的时间数量问题。从情感突显出发,学习时间的质量更关键」。事实上,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keeley能在20种不同语言中自由转换的原因。
在所有的多语者中,michael levi harris可能最好地展现了这些原则。harris是一名演员,经过不断的训练,他精通10门语言,还较熟悉另外12门语言。偶尔,他的激情也让他陷于困境。有一次,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马耳他见面会的广告。于是,他想借此认识一群来自马耳他的人,结果,却走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全是中年妇女和她们的马耳他狗——他把这段经历在短篇电影「the hyperglot」重演了一遍。下面是电影的预告片。
当我在伦敦市政厅音乐和戏剧学院附近的一个咖啡厅和他碰面的时候,他毫不费力地操着一口标准的英伦音,虽然他是一个地道的纽约人。他在说话的时候,他的姿势随着他融入的新角色而变化。「我并没有刻意地去改变我的性格和我角色。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但我也清楚我是确实不一样了。」
重要的是,harris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纳一种新的文化——基于他演员的经验,他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如何开始。他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考虑单词拼写地去模仿。「每个人都能听和复述」,他说。你可能会发现这有点夸张,就跟一位演员最开始表演时有点演过了一样——但这是关键性的一步。他还说:「最开始演的时候,你夸张点,随后导员会说好,然后就慢慢平实一点。再把这个运用到学习语言中去」。他还建议要善于观察,如面部表情——因为它们对发声起着关键的作用。比如,说话时微微撅起嘴唇可以让我们的声音更有法国情调。
最后,他还说我们应该尽量去克服发「怪」音的尴尬——例如阿拉伯语的喉音。「你必须意识到这并不是外来的——当你觉得很恶心的时候,你已经会发『呃』这个音了。如果你承认并下意识地允许自己说出来,你就能发出这个音了。」这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蠢,但重点是所有的这些都能够帮助你克服你本身的自然抑制。「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拥有语言,就如演员一样必须使观众相信所有的语词都是你自己的。当你拥有语词的时候,你说话就更有自信,人们也会愿意接近你。」
并没有一个决定因素会阻碍人们高效学习其他语言
即便如此,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不能过于雄心勃勃,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硬要说有一个因素阻碍着人们高效学习其他语言,那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像母语者一样的心理——这个标准遥不可及,却一直笼罩着我们,」坦普尔大学的pavlenko说,「有一句通俗的话对于我来说很重要——那就是口头上,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表达自己。」
照着这样的路径,我们还应该经常短时间地练习——也许就15分钟一次,一天四次。「我认为和运动类比也是很不错的,」alex rawlings说。他和richard simcott合作发展了一系列多语者工作坊,教给他们技巧。simcott说:「即使你很忙或者很累,不能认真学习,仅仅练习一段对话或者听一首外文流行歌都会有所帮助。」
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很容易就认为我们并不需要付出那样的努力。事实上,在我遇到这些「hyperglots」之前,我一度怀疑他们的痴迷值不值得这样的努力,我认为他们大概仅仅是为了有吹牛的资本。但我当遇到的这些「hyperglots」,他们是真心热衷于沉浸在其他语言中——这也带来了惊人的回报,包括交更多朋友,取得更多联系,甚至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
举个例子。harris就描述了他生活在迪拜的经历。「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在中东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最后,我却与一个来自黎巴嫩的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他说,「当我要走的时候,他对我说『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成为朋友,而现在你要走了,我很是难过』,与你之间的友谊是我最宝贵的回忆。」
judith meyer组织这次柏林聚会,她告诉我,她看见乌克兰人、俄罗斯人、以色列人和巴基斯坦人在聚会上都积极交谈着。「学习一门其他语言真的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